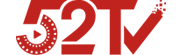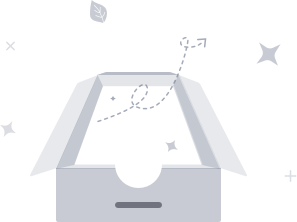这部排片率

4月2日,世界孤独症日,纪录片《特别的你》上映。导演翁羽表示:“我从来不认为,一部电影会有多大的力量去改变什么东西。但现在我有点不这么想了。”
七八个孩子站在台上,有的在跑,有的在哭,有的在笑,有的则愣在原地,眼神呆滞。
这是翁羽在为小说采风时看到的情景。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,翁羽从事电影相关工作,做过美术指导,执导的第一部短片在莫斯科电影节上映;也举办过当代艺术展,去年在全国范围展出。
2021年,翁羽计划写一本关于自闭症儿童的小说,经朋友介绍,他来到一家特殊学校采风,见到了上述场景。 不久后,他到了另一家收治重症孤独症患者的特殊学校。逗留的大半天里,他看到一个成年男子在课堂上突然脱裤子撒尿,也见到一个小孩用后脑勺撞墙,被老师带回去后,不知道怎么又跑回原处,重复头撞墙的动作······
他跟一些家长接触过,发现他们有同样的想法:孩子确诊后,首先想抱着孩子去死,有人真的付诸过行动;其次,是希望比孩子多活一天,因为他们担心自己死后,孩子也没法活下去。而且,每个孤独症患者及其家庭都遭受过亲友或陌生人的歧视。从确诊书下达那一刻开始,异样的眼光就伴随了他们其后的每一天。
他决定把自己了解的这一切拍成片子,“我也成不了张艺谋,就想做点有价值的事。”

翁羽(右)在拍摄现场。(图/受访者提供)
过去四年来,“孤独症谱系障碍”(以下简称“孤独症”)逐渐走进大众视野,相关讨论也越来越多。但实际上,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孤独症患者群体及其家庭,仍是未知数。因为拍片,翁羽频繁接触这一圈子。据他评估,他身边至少有80%的人不了解孤独症,甚至有人以为这是一种心理疾病,表现为不爱说话、不爱理人。大家对这个词并不陌生,但又谈不上真正了解,也没有机会去了解更多具体情况。翁羽说:“他们这些人都被雪藏起来了。”
此前,关于孤独症的纪录片、影片并不少,而《特别的你》是首部登上院线的纪录片。公开上映,意味着能被更多人看到。但是,纪录片毕竟是小众题材,从商业的角度看,选择它无疑是“赔钱的买卖”。
灯塔专业版显示,截至目前,全国安排场次仅为90场,当日排映院线数为28个,排片总占比<0.1%,场均人次19.3。

(图/灯塔专业版)
首映前一晚,广州市区唯一一家有排期的影院,在原定播映时间前16个小时取消了场次,票款原路退回。购票平台显示,一家位于广州黄埔区的影院有安排上映,场次为20:05,暂无人购票。此外,北京无院线上映,上海和深圳均仅有一家影院可以观看。
在超一线城市的播映情况都不乐观。“这个电影注定不可能在院线上取得什么样的成绩,这是最开始做我就知道的,所以我也不太关注具体的数字。”更何况,翁羽觉得,做这个片子,实际上收获比意想中多。
那些“习惯性隐藏”的人
决定做这件事的第一天,翁羽就觉得一定能做成,因为这是一件有价值的事。
制作电影需要拉投资。筹备的那半年时间,无人看好这一项目,找不到人愿意资助。翁羽于是和几个朋友商量,那就自掏腰包,凑钱做。他们经常把做其他项目挣到的钱补贴进来,偶尔有企业送来两箱水,也统统接收。“像要饭的”,翁羽笑着说。
他形容拍片过程就像西天取经,“要饭”要不来、被拒绝都是家常便饭。但他心里认定了这件事,不管碰到什么事情,哪怕自尊受伤害,也只有一个念头:一定要做出来,让大家看见这个群体。
这么一想,资金反而不是最大的问题,最难的是取得孤独症患者家庭的信任。翁羽走访了500个家庭,从中挑选被拍摄的对象。然而,被拒绝的理由总是相似的:很多人,尤其是父亲们,不太愿意让自己的生活被记录,总是习惯性地隐藏起来。

(图/《特别的你》)
和孤独症患者家庭的交涉过程中,翁羽总会提到一个例子。在北京,他几乎不带狗去商场或饭店,因为鲜少有公共场所允许宠物进入,狗总是被拒之门外。但在重庆,所有的饭店和商场,无论大小,都对宠物开放。在那里,他感觉出门不带狗反而对狗不公平。这不是因为城市本身有什么区别,而是环境对生存和生活的影响。
他反复解释,告诉家长们:如果没有人站出来,他们就会永远面对同样的问题。部分家长担心给别人添麻烦,翁羽认为,如果大家都不接纳他们,孩子们就会越来越被孤立在自己家里,情况也越来越糟。
有四个符合拍摄需求的家庭同意接受拍摄。但开机后,翁羽悬着的心还没放下。他始终担心,在拍摄过程中,有的家庭感觉受到冒犯,会突然不愿意让他们进入。另一种情况是,有些家庭的故事可能不够精彩,或者比较平淡。毕竟,这是一部有记录性质的电影,不同于纯记录、写实的纪实作品,它需要适度的故事性和编排。
成片中确实删掉了其中一个家庭的故事线。那是一个离异家庭,男方重组了新家,有了新的孩子。翁羽很想拍这部分内容,那个爸爸对两个孩子的态度肯定有所不同,而这种差异如果展现出来,可能会引发很多问题,给那个家庭带来巨大的压力。这条线最终没有拍成。

(图/《特别的你》)
“几乎每天都哭一次”
资金、人员和团队,最难的前期任务完成,而意料之外的挑战还在后头。
翁羽会跟拍摄对象提前讲解可能遇到的情况,告诉他们拍摄会打扰他们的生活,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。他们都表示理解并接受。
为了以防万一,第一周,翁羽特意加强了拍摄强度,让拍摄对象体验这种被拍摄的感觉,向拍摄对象提出如果他们接受不了,可以做出相应调整。比如设置多个机位,从早拍到晚,甚至睡觉的时候也会拍——总之,拍摄对象干什么、去哪儿,都会跟着拍。
有一个情节:片中一个人物的父亲,因无法接受孩子患病而跳楼自杀。拍摄时,父亲已经离世,但这一背景故事对观众理解情节至关重要。纪录片不能通过演绎或重拍来呈现,因此,他们询问拍摄对象是否可以拍摄他和家人去墓地祭奠父亲的场景,对方答应了。至于他们到了墓地后怎么做、说什么,摄制组完全不干涉,因为这是他们真实的情感表达。
翁羽解释道,这一情节本身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,只是在时间上做了调整,以强化拍摄效果。翁羽拍摄时发现,他们都能接受这种安排,还很配合。翁羽觉得,参与拍摄的家长都有种使命感,“他们知道他们代表了1000多万个家庭。”

(图/《特别的你》
家长配合,那孩子呢?孤独症孩子不可控,只顾自己不管别人,似乎是大家普遍的想法。
一开始,翁羽想过孩子们会捣乱,或者出现一些难以预料的状况。实际上,他担忧的情形一个都没出现。被拍摄的孩子们都对摄像头不感兴趣,他们对设备背后的人有兴趣。
比如,出发去某个地方时,正常情况下,一个人进了电梯,如果没有其他人,他就会按电梯走了。关上电梯门的瞬间,是摄制组想呈现的画面。但电梯门一打开,那些孩子总是会摁住开门键,等待摄制组进入,因为他们知道有人在拍他们,他们应该是一起行动的。
孤独症的孩子还普遍有刻板行为。他们会要求东西必须摆放在某个位置,几点起床就得几点起床,几点睡觉就得几点睡觉,认定的事不能改变。
一位家长提过,做饭时,如果把土豆丝做成土豆片,那不行,必须重新切,否则孩子就不吃。孩子对土豆丝的宽窄还有严格要求,一定要足够精细。还有家长在带孩子外出时,如果电瓶车在路上突然没电,孩子就接受不了,会在地上打滚、哭闹。因为孩子认为,电瓶车必须有电,他不理解为什么会没有电。类似事情一旦在公共场所发生,家长的耐心将面临极大的挑战。
对翁羽来说,拍摄过程中,印象深刻的事情每天都有,实在太多了。他自述,作为一名男性,一年多的拍摄时间里,他几乎每天都会在监视器后哭一次。

摄制组进行拍摄。(图/受访者提供)
“选到谁就是谁”
孤独症患者家庭的艰辛、无奈,种种情绪都直击翁羽的内心。他表示,刻骨铭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,多到他都记不住。
很多孤独症患者家庭不止一个孩子。有些家长在面对这种情况时,会选择再生一个孩子,希望新生的孩子能够为患病的孩子提供支持和帮助。但世事不一定如愿。翁羽遇到过类似情况:老大是孤独症患者,老二也是,而且症状更重。这对家庭来说,无疑是沉重的打击。
于是,除了主要照料者(父母)和患者,影片的镜头还落在患者的其他兄弟姐妹身上。
其中一个家庭,姐姐不是孤独症患者,但妹妹是,且症状严重。姐姐努力学习,成绩很好,但她明确表示,将来不想结婚,而是希望带着妹妹一起生活。
某种意义上说,那些作为平辈、需要照顾孤独症患者的人,他们从出生起就背负着巨大的压力,这对他们而言极不公平。翁羽举例,如果弟弟结婚后,要把患有孤独症的姐姐接到自己家中生活,配偶不一定能接受——毕竟,多数人对此是难以接受的。这是这些家庭很拧巴的地方,伦理将他们捆绑在一起,无法挣脱。

(图/《特别的你》)
在翁羽看来,孤独症患者是天选之人,“选到谁就是谁”。最让他感到无力的是来自社会的包容和支持还不够。因此,选择拍摄对象时,翁羽就有意识地根据不同年龄患者所需的外界支持进行筛选。
12岁的程瑞有绘画天赋。妈妈曾在生父的拳头下用身体护住他,如今一个人种菜养家,只希望程瑞能和正常孩子共同学习。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压力,以及在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的困难。16岁的可可几乎不会说话,只能说出“妈妈”,无法上学。因此,她面临的问题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区支持不足。19岁的王浚力已经从特殊学校毕业,有一定独立生活能力,但缺乏就业机会,只能待在家里,无法自食其力。
此外,这三个家庭都有各自的故事,包括家庭结构、夫妻关系等。有一个家庭的丈夫去世,母亲希望重新开始,寻找新伴侣,建立新家庭;另一个家庭,父母很早就离婚了,由于带着孤独症孩子,双方都很难再找到合适的伴侣,他们试图修复感情;第三个家庭是符合传统定义的“完整家庭”,父母双方健在,还有个健全的小女儿。
虽然家庭情况不同,但面临的困境却是相似的。归根结底,孤独症不能治愈,经济条件再好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。

(图/《特别的你》)
许多家长希望孩子能进入普通学校而不是特殊学校接受教育。但进入普通学校非常困难。即便孩子进了普通学校,其他家长也可能会有抵触,担心这些孩子会对自己的孩子产生不良影响,甚至有攻击行为。这种情况下,校方也很无奈,虽然他们支持融合教育,但也有自己的难处。
每个人都有基于自己的立场,可是,孤独症孩子也有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。
在拍摄和采风过程中,翁羽看到过许多孤独症孩子被歧视的情景。他们可能会因为不懂得分享或尊重他人,而被误解,甚至被打骂。
例如,有些孤独症孩子喜欢喝饮料,但他们可能不知道饮料需要购买,也不知道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。他们会在别人喝饮料的时候上手抢,或者在别人喝完了将饮料瓶顺手放在公园里时拿走。万一他们不小心把别的孩子推倒,其他家长可能会误解他们,甚至对他们采取极端手段。
“这种故事在这个群体当中都是常态。”翁羽设想,如果公众能更多地了解孤独症群体,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。
他听说,有些机构倡导在孤独症孩子的衣物上设置标识,以便大家能理解他们的行为。从外貌上看,孤独症孩子和普通孩子没有区别,只有当他们出现极端行为时,人们才会意识到他们与众不同。如果有标识,大家可能会更理解他们的行为,而不是采取过激反应。

(图/《特别的你》)
“这是你拍的吗?”
影片最后一个镜头,拍的是一座没有装修好的房子。一个人要搬进这座房子里,镜头是主观的——从毛坯房到阳台,推向人物。
在翁羽看来,孤独症孩子只是还没完成,或者说还没有达到常规价值观中“完整的人”的最后一步。这是全片中少有的、具有作者性的一幕。另一幕则出现在开头——程瑞走丢了,妈妈在街上到处找他。
虽然全国1400万孤独症患者看上去像一个被遗忘的群体、一座孤岛,但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。每个患者至少牵动着两个家人,甚至更多。这么算下来,所涉及的人群可能达到上亿人。就像岛与岛之间是相连的,他们之间也有着相互的联系。
旁观者能做到的,就是让公众更多地了解并接纳他们。在影片预告片的评论区,有一条令人印象深刻的评论:对于这个特殊群体,尤其是儿童,他们不需要电影,而是需要能够落到实处的政策。
翁羽认为这是人的本性。就像普通人,如果得了绝症,很多人不会到处去讲,而是选择自己默默承受。但如果一个人能够走出来,那他应该是很坚韧、很强大的。当然,多数人还得需要时间消化。
如何才能让他们更快地走出来?他觉得关键在于社会的接纳。以前,一个男士喷香水可能会被视为怪异,但现在这种观念已经完全改变了。如果社会的信赖度越来越高,我们的文明程度也不断提升,那么这些问题可能就不再是问题了。也许,未来这部影片的存在价值就没有那么大了,但至少现在它还是有一定价值的——它能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个群体。

(图/《特别的你》)
影片已经上映,但翁羽至今还没能统计出具体花费的成本,“还在花钱”。
宣传期出席活动的差旅费用,很多时候需要自行承担。翁羽表示,自己是“贴钱在做这件事”。不过,他不愿意视之为一个买卖。正如父母将子女养育成人不能简单地用成本来衡量,当一个人真正热爱一件事的时候,成本就不再是成本,而是为这件事情付出的决心。到了那个程度,就不会再去衡量得失。
他只是遗憾,如果有足够的资金,成片效果可能会更好。比如,在声音、画面、色彩等技术方面处理得更好;摄影师也不会因为生计问题而接其他活儿,可以全身心地投入。资金虽然不是决定性因素,但它确实能让影片的成色更好,让整个创作过程更顺利。
他还提出做融合观影活动,让孤独症患者家庭和普通家庭带着孩子一起在电影院观看这部影片。目前,全国多地已经举办了好几场观影活动。
第一场观影活动的组织者跟翁羽聊起,他们平常就有组织观看小众电影的习惯,但当他们发起这部电影的观影活动时,有些人一开始就不想参加,还有人因此退群。
在观影活动现场,确实有一些观众感到不适。因为孤独症孩子可能会比较活跃,不太安静,而有些观众原本是带着艺术欣赏的期待来的,希望有安静的观影环境。结果他们发现,银幕上和银幕下都很“热闹”,可以说是真正的“4D电影”。
活动结束后,通过和孤独症患者进行短暂的交流和沟通,观众开始接纳他们。在翁羽看来,这就是做融合观影活动的意义所在。

在江西赣州举办的观影活动。(图/受访者提供)
《特别的你》于2024年7月入围FIRST青年电影展主竞赛单元。之后大半年来,影片经由部分公益机构、相关政府部门、企业和高校进行点映,并于今天正式在院线上映。根据灯塔专业版的统计,截至发稿时,《特别的你》票房达32.7万元。
据翁羽估算,有上千万人知道了这部电影,其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他的预期。多年没有联系的发小、老家的朋友,有些甚至连微信都没加的人,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这部电影,主动跟他说:“这是你拍的吗?”
他最初的设想是通过这部影片宣传孤独症群体,让更多人了解他们。他觉得这个目标已经部分实现了。最让他意想不到的是,影片不仅引起了关注,也实实在在地帮助了这个群体。
很多企业、团体和政府部门通过包场观影的方式,来了解这一人群的困境,并开始在政策、资金、就学、就业等方面提供实际帮助。“我从来不认为,一部电影会有多大的力量去改变什么东西。但现在我有点不这么想了。”翁羽说。